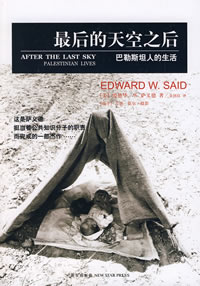编辑推荐
这是萨义德,担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而完成的一部杰作……
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闻。他们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凶残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惨的难民。萨义德在本书中描绘出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肖像:从以色列的建立到贝鲁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连续的土地剥夺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这其中也包括萨义德本人及其亲人的真实遭遇。作者指出:新的巴勒斯坦自我身份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身份上,相反,它将在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感上。
内容简介
并非没有人谈论或描写过巴勒斯坦人,大量的文字已经形成、但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号召武装的借口。在大多数人那里,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他们的真实依然鲜为人知。
爱德华·W.萨义德,卓越的文化批评家和美国最著名的巴勒斯坦发言人,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他用他的文字,连同吉恩·莫尔的摄影,描绘出了动人的巴勒斯坦民族像。从以色列国的建立到贝鲁特的堕落,巴勒斯坦人如何连接地遭受驱逐,不断地从一处地方、一段过去、一个家撤离。但在这苦难的流亡史中,萨义德也辨认出了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迹象,不再基于离散或苦难,而是基于坚持、希望和觉醒的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
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巴勒斯坦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l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后移民美国,1963年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终身教授。2003年9月24日,与白血病抗争10多年以后去世。
主要著作有:《东方学》(Orientalism,l978)、《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nafism,1993)、《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The l993 Reith Lectures,1994)、《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1969-1 994)》(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il: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if—Determination,1969-1994,1994)。
目录
致谢
前言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第一章 国家
第二章 内部
第三章 涌现
第四章 过去与未来
后记 贝鲁特的衰落
媒体评论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马哈穆德·达威什
书摘插图
第一章 国家
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月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部战斗所破坏。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一个代表德国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奢侈品,但在累范特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梅赛德斯承担起了马匹、骡子和骆驼的职责,甚至更多。梅赛德斯在这里被当作是通用的出租车,标志着被本土化的现代科技、西方对传统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最后的通道。”
迁移和不安之问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悲惨地比过去更加糟糕。他们或者是“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有些被称作是“在场的缺席者”。在除了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发放特殊的卡片来鉴别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即使在那里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技师,他们知道在他们东道国的眼中,他们将永远是外国。不可避免地,拍摄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包含和显示了这一事实。
回忆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离散的从未减轻过的强度。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袭击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在他们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无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精巧模糊的苍白相互冲撞。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就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状中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
有时面对重新定居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痕迹上书写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就座于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提起,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迫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没有姓名而且无声沉默。当我注视着它们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精确的信息和知识,但是它们现实主义的精确却比单纯的信息留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这些被拍摄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个欧洲摄影师为我来观察他们。我想象他,通过翻译依次和他们交谈。然而,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他们对他十分礼貌,或者表现出那样的倾向,好像他是导致他们如此悲惨的那些人之一似的。人们感到很窘迫,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观察和记录。然而,他们却无力去制止这一切。
当A.Z.的父亲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子女叫进房间,进行最后一次家庭聚会,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娶了我的姐姐。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虚弱的老人,来自海法。他最后的34年都在贝鲁特度过,始终激动地不愿相信他已失去了房子和财产。如今,他对子女们喃喃低语着,这是一位贫穷无助的家长颤抖的最终遗言。“拿好这些钥匙和契约,”他一边指着床边那个破旧的箱子,一边告诉他们。箱子里储藏着当海法的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境时,他自巴勒斯坦抢救来的家族财产。这些关于过去的亲密的纪念品在我们当中已经无可挽回地不再流传,就像是流浪歌手吟唱的家谱和神话一样。照片、衣服、从原先场所分离的物品,以及说话和风俗的例行习惯:被大量复制、放大、主题化、添油加醋,并且广为传播,它们缠丝结网,被我们巴勒斯坦人用来维系自己和我们的民族身份,联系彼此。
有时,这些带着沉重回忆的物品——照相簿、祈祷的念珠、头巾、小盒子——对我来讲似乎是些累赘。我们携带着它们到处迁移,把它们悬挂在每一个新藏身处的墙上,钟爱地想着它们。这样我们就不去注意痛苦,尽管痛苦仍然在继续和不断加重。我们也不会去承认自己心态已经被冻结得一成不变。最终,过去掌握了我们。我的父亲倾其一生想要摆脱它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实际的地点以及复制和人造的本质。父亲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整个家族都出生在耶路撒冷。父亲是一个老城的孩子,向游客们兜售真十字架和用荆棘编织的皇冠。但是他仇恨那个地方,他常说那个地方意味着死亡。父亲几乎没有任何从那个地方留下的东西,只除了一两个断断续续的故事、一枚零碎的硬币或纪念章、一幅祖父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以及两块小毯子以外。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一幅有祖母面容的照片。但是当父亲逐渐年老,他开始使用旧式耶路撒冷人的措辞方式,我听不懂也从来没有在年轻时听说过它们。
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很难在流散中继续维持。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但巴勒斯坦人却不能,他们或多或少经常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人们不仅视我们为恐怖分子,而且否认或者质疑我们作为巴勒斯坦土生的阿拉伯居民,在巴勒斯坦(而非其他地方)拥有基本的权利。不仅如此,人们把我们的存在负面地和对以色列民主、成就及活力的赞美联系起来;在西方大量修辞中,我们被偷偷地称作是一个充满纳粹党和反犹太人的地方;我们全体除了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悄无声息和迁移,再无其他渴望。除了扰乱中东和平的厚颜无耻的行为以外,我们以缺乏实际成就和没有让人尊重的特性而著称。一些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说:“巴勒斯坦人可以待在这里,但是不能拥有任何权力,只能作为定居的外国人。”其他以色列人甚至更不仁慈。我们没有著名的爱因斯坦、查格尔、弗洛伊德和鲁宾什坦,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我们也不曾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党屠杀的大灾难,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我们是“其他的”和相反的,是大批离开和迁徙的几何图形中的瑕疵。沉默和谨慎掩盖了伤害,减缓搜索尸体的速度,也抚慰了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刺痛。
巴勒斯坦内只有少数几个地方,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没有改变,人们可以重新回忆起过去的快乐。偶然不经意的一瞥,那些兜售蛋糕和蜀黍的小贩们仍然在那里,仍然挑起人们的胃口。他们似乎不仅从一个地方游历到另一个地方,也从过去穿越时光来到了现在,带来和过去同样的顾客——年轻的女孩男孩,正在回家路上的骑自行车的人,到处闲逛的学生和职员。和过去一样,我们用偷偷发现的零钱(谁能记得是什么货币单位?是比索?费斯?先令?),从小贩那里买来的既不是品质特别优良、也非经过精心烹饪的食物。沾着气味浓烈的百里香和漆树草混合调料的圆形芝麻蛋糕,或是撒着盐的煮蜀黍,品尝小贩出售的这些食品是一种奢侈的愉悦,它超越了进食这一纯粹的行为,在我们展现了食物全然令人愉悦的滋味,这种滋味和进食、汲取营养以及例行常规毫无关系。然而如今,我和那种生活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如此巨大。照片似乎多么轻易地传播,而把我阻挡在照片中场景的障碍又有多少可能去清除。
因为这片土地比它从前更加遥远。我1935年末出生于耶路撒冷,1947年底我永远地离开了托管下的巴勒斯坦。1948年春,我最后一个堂兄弟也从我们家族在西耶路撒冷的房子里撤出。听说,马丁·布伯后来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过世。我在埃及长大,之后来到美国求学。1966年我来到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参加一个家族婚礼。我的父亲也陪着姐姐和我去了那里,在那次婚礼的5年后,父亲离开了人世。自从那次旅行以来,我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搬迁到了新的地方,搬去约旦、黎巴嫩、美国和欧洲。据我所知,我的亲戚当中已经没有人还居住在曾经的巴勒斯坦。战争、革命、国内斗争,把我曾经居住过的国家——黎巴嫩、约旦、埃及——改变得面目全非。直到35年以前,我还能够走陆路从开罗前往贝鲁特,穿越被敌对殖民势力占领或通过其他办法控制的区域。如今,虽然我母亲还住在贝鲁特,但自从1982年的以色列入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她: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已经不再受欢迎。事实是,如今我既不能够返回我少年时居住过的地方,也不能够在那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自由旅行。在这些我过去经常出入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和政策最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使得我们随时可能遭受逮捕或暴行。现在,再也没有比进入一个阿拉伯国家时遇到的海关和警察检查更让我不愉快的事情了。
想想自1948年以来发生的巨变,每一次都有效地毁灭了我们过去生存的环境。当我出生时,我们在巴勒斯坦感觉自己属于一个小社会团体,由主流团体和这个或那个控制该区域的外部势力所主持。比方讲,父亲和我都是一个很小的基督教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存在于一个大许多的希腊东正教…少数派,而这之外则是更大的伊斯兰逊尼教多数派;而重要的外部势力则是英国,以及仅次于它敌对的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和法国失去了他们的统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直接面对殖民的遗产——无能的统治者、四分五裂的种族,以及殖民者对拥有相反主张的阿拉伯居民和大部分欧洲犹太人所许下的相互冲突的诺言。1948年,以色列成立;巴勒斯坦遭到摧毁,巴勒斯坦人遭受剥夺的悲惨经历从此开始。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导致在那里剩下的大批累范特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美国人、叙利亚人)被迫离开。阿卜杜尔·纳赛尔的崛起点燃了所有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复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希望,然而当1961年叙利亚和埃及的短暂联盟失败后,所谓的阿拉伯冷战真正开始;沙特阿拉伯对抗埃及,约旦对抗叙利亚,叙利亚对抗伊拉克……新的难民、流动工人和到处旅行的政党在阿拉伯世界中交叉往来。而我们巴勒斯坦人则沉浸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以及黎巴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等各种政治当中。
1967年战争之后不久就是阿拉伯石油的迅速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兴起成为中东地区的一支独立的力量。我们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充满希望。然而,这种兴起实际上导致了大量不健康的现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马龙教民族主义,以及犹太教坚贞主义。如果没有造成这些现象,我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表现也会及时地大大增强。新消费文化和电脑化的经济,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中令人吃惊的贫富不均、新旧不等,以及特权阶层和权力被剥夺人群之间的差距。接着,从1975年开始,黎巴嫩内战使得黎巴嫩国内的不同教派、巴勒斯坦人以及大量阿拉伯和外国势力陷入了彼此的斗争。贝鲁特作为阿拉伯生活的智力和政治神经中心被摧毁;对于我们而言,这是我们唯一重要、相对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中心的终结,其核心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瓦尔·萨达特承认以色列,而戴维营则进一步瓦解这个地区的联盟,扰乱了它的平衡。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两伊战争随之而来。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使得更多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移。而在萨布拉-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发生的大屠杀进一步减少了巴勒斯坦人群的数量。到1983年底,巴勒斯坦人内部发生战斗,叙利亚和利比亚被直接卷入,支持巴勒斯坦反对派抵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商品评论(0条)
内 容:
购物评价
所有评论都来自购买本商品用户!你要登陆后才可以发表评论登录|注册
支付方式
多种收款方式 支持外卡,7X24小时客服 技术支持快速反应 支付更简单,交易更安全,结算更及时!
 已有0人评价
已有0人评价![]()